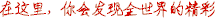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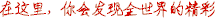

您当前位置:华人舞蹈网_体育舞蹈-体育舞蹈视频 >> 舞蹈资讯 >> 舞蹈评论 >> 浏览文章
跟百乐门的无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舞林大会》的热潮。持续了一年的《舞林大会》刚落下帷幕,收视率狂飙到14点,把热门电视剧都甩到后面。由此引发的学舞热潮,让上海各个国标/交谊舞校应接不暇,可以说上海教舞这个行业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牛市。可惜的是牛市救不了一个百乐门,本人习舞十多年,对其中的缘由看得清楚。
国标也好交谊舞也罢在中国大陆已经落寞多年了,一方面是公园里广场上每天早晨蔚为壮观的中老年练舞方阵风雨无阻持之以恒,一方面是最具消费能力的年轻白领对它嗤之以鼻。我的舞蹈教练认为,是最早一批搞国标舞的把这个行业弄坏了。他们都是专业舞者,不懂经营,以薄利多销为指导思想,用萝卜青菜的价格吸引来的只是一些低收入者。在露天公园里跳一场,五块钱就够了,不给也无所谓;文化馆、街道甚至居委会都可以开舞会,消费也就一杯茶的钱。所以会有这种怪现象:很多舞场里的舞客有一半是下岗工人!他们专捡日场跳。
上海高档点舞场的以前有大都会(梅龙镇伊斯丹),泰兴路政协礼堂,南京西路的海员俱乐部,延安西路展览中心,门票最贵的也就50元,先后都关门大吉。就算最高档如百乐门,内部装修号称华丽其实恶俗无比,200元的高价门票(只含一杯饮料),提供的乐队歌手根本没法听。
去年百乐门公开招聘为舞客伴舞的“舞师”,一度引发很大争议。现在舞厅里的一块电子显示屏上,不断地跳跃着“本月皇后XXX,本月贵妃XXX,本月格格XXX”,恶心你不偿命。
放眼望去,舞池里的舞客还是身材走样涂着厚粉的中老年妇女居多。有个叫唐阿姨的,七十多了,每场不拉,年轻时也是上海名媛,其姐跟陆小曼当年号称“南唐北陆”。年轻人偶尔来一次,也是好奇,来过了,就得出结论——这不是他们的地方。
“月明星稀,灯光如练;何处寄足,高楼广寒;非敢作遨游之梦,吾爱此天上人间”,这是1932年百乐门刚建成时,一位不知名的诗人留下的传颂一时的诗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座“远东第一乐府”的仰慕。
百乐门当年举行开张典礼时,市长吴铁城亲自出席发表祝词。到百乐门跳舞一时成为上流社会时尚,许多名人留下踪迹:张学良、徐志摩时常光顾;陈香梅与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在此举行;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慕名到此跳舞。百乐门还拥有许多出色歌星,梁实秋晚年的妻子韩菁菁11岁那年,就曾在3000多名应考者中脱颖而出,成为百乐门“一代歌后”和“大众情人”。百乐门乐队在当时首屈一指,大胆起用中国第一支华人乐队——吉米金乐队。当时舞女的月收入高达三千至六千元,是普通职员的十倍以上。
当年百乐门没有停车场,车子只能停在远处小马路等候。为方便舞客,百乐门在顶上的玻璃银光塔装了许多灯泡,串成一个个数字。每辆等候的车子对应一个数字。司机看到自己的车号在灯塔上亮起来,便知道主人要离开了。1952年百乐门改为红都电影院,这一沉寂就是几十年。
2002年百乐门舞厅重新开张,正好顺应了当时浓烈的上海怀念30年代风,却没有梅开二度,我认为是经营者失策。拿国标和瑜伽相比,瑜伽一进入中国大陆就是披着时尚的外衣, VIP年卡可以卖到五千、一万,一开始抓的就是年轻人的钱,真正把瑜伽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传递给消费者。而国标至今不是年轻人的社交手段,《舞林大会》引发的牛市也是昙花一现。纵然是爆棚的各个舞校,学员也清一色是女白领,男女比例通常都是1:9,2:8。学完了没地方跳,更没有男舞伴。百乐门的风流,终究是雨打风吹去。